“你别弄错了。”神父说。“我在什么事情上弄错了?”K问。“在法院这件事上你弄错了,”神父说,“在法律的前言里,提到过这种错觉:在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乡下人来到这个守门人面前,请求见法,但守门人说现在不能允许他进去。那人考虑了一下,然后问他之后是否能被允许进入。‘有可能,’守门人说,‘但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往法律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而守门人站到一边,那人弯下腰,想望进那扇门里。守门人发现了,便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么尽管我禁止,你还是可以尝试进入。但是要知道:我的力量很大。而且我只是最低阶的守门人。从一个厅到另一个厅,站着一个比一个更有力气的守门人。第三个守门人,我光是看到他的样子就承受不了。’
那个乡下人没有料到这等困难,他以为法律应该是人人都可以随时接近的。当他更仔细地打量那个身穿毛皮大衣的守门人,那大而尖的鼻子,长而稀疏的鞑靼人黑胡子时,他决定还是宁可等待,等到他获得进入的许可。守门人给了他一斟凳,让他坐在门的侧边。他在那儿坐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一再尝试获准进入,一再央求,让守门人不胜其烦。
守门人经常对他进行小小的盘问,询问他关于他家乡的事和许多其他事情,但那是些漠不关心的询问,就像大人物所提的问题,而到最后,守门人总是说还不能够让他进入。那个人为这趟旅行带了许多东西,他把一切都拿来贿赂这个守门人,哪怕是再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吝惜。守门人虽然把东西全都收下了,却在收下时说:‘我收下来只是为了让你不要以为有什么该做的事自己没做。’在那许多年里,那人观察着那个守门人,几乎不曾间断。他忘了其他的守门人,在他看来,这第一个守门人是进入法律的唯一阻碍。他咒骂这不幸的巧合,在头几年里很大声,后来他老了,就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他变得孩子气,由于他在对那守门人的长年观察中也发现了对方毛皮领子上的跳蚤,他也央求那些跳蚤帮他的忙,去改变守门人的心意。
最后他的视力变弱了,而他不知道四周是否真的变暗了,还是只是他的眼睛在欺骗他。不过,如今他在黑暗中看到一道光,源源不断地从那扇法律之门里透出来。现在他活不了多久了。在他死前,这些年来的所有经验在他脑中集结成一个他至今不曾向那守门人提出的问题。他向那守门人示意,因为他僵硬的身体已经无法站直。守门人必须深深地朝他弯下身子,因为两人的高矮差别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人变矮了。‘现在你还想要知道什么?’守门人问,‘你永远不满足。’‘明明大家都在追求法律,’那人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除了我都没有别人要求进入呢?’守门人看出这人的已经到了尽头,为了让逐渐丧失听力的他还能听见,向他大吼:‘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在这里取得进入的许可,因为这个入口是专门为你而设的。现在我要走过去把它关上。’”
“所以说,守门人欺骗了那个人。”K立刻说,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不要操之过急,”神父说,“不要未经检验就接受别人的看法。我把这个故事根据原文所写的讲给你听,那里面没有提到欺骗。”“可是事情很清楚,”K说,“而且你最初的说明完全正确。守门人直到最后才做出能够拯救他的告知——当此一告知再也帮不了那人的时候。”“他之前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神父说,“你也要考虑惮他只是个守门人,而身为守门人,他尽到了他的义务。”“你为什么认为他尽到了他的义务?”K问,“他没有尽到他的义务。他的义务也许是拦住所有的陌生人,可是入口既然是为这个人而设的,他其实应该让他进去。”
“你对那篇文字缺少足够的尊重,更改了那个故事。”神父说,“针对进入法律的许可,故事中包含了守门人所做的两个重要解释,一个在开头,一个在结尾。一处说的是:‘现在他不能允许他进入’,另一处是:‘这个入口是专门为你而设的。’假如这两个解释之间互相矛盾,那么你就可以说守门人欺骗了那人。然而这两个解释之间却并没有矛盾。正好相反,第一个解释甚至预示了第二个解释。几乎可以说,守门人超出了他的义务,向那人提出了将来允许他进入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他的义务看来只在于阻挡那个人。
的确有许多解释那篇文字的人纳闷那个守门人居然做了这样一个暗示,因为他似乎重视精确、严格地守护他的职责。那么多年他都没有离开岗位,直到最后惭门关上,他对于自己职务的重要性十分自觉,因为他说:‘我力量很大’。他敬畏上级,因为他说:‘我只是最低阶的守门人’。只要涉及善尽义务,他既不会被打动,也不会被激怒,因为文中说那人‘一再央求,让守门人不胜其烦’。他不多话,因为在那许多年里,他只提了些如文中所说‘漠不关心的询问’。他不被收买,因为对于那人送他的礼物他说‘我收下来只是为了让你不要以为自己少做了什么该做的事’。最后,他的外表也暗示他的个性拘泥细节,那大而尖的鼻子,还有长而稀疏的鞑靼人黑胡子。还会有比他更忠于职守的守门人吗?
不过,在这个守门人身上还掺杂了别种性格特征,对那个要求进入的人十分有利,而且这些特征也让人至少能够理解,他何以在暗示将来的可能性时会稍微超出了他的义务。因为,无可否认,他有点头脑简单,并且因此而有点自负。他针对他的力量以及其他守门人的力量所说的话,还有他说自己承受不了第三个守门人的模样——就算这些话本身都没有错,但他说这些话的方式却显示出头脑简单和自大蒙蔽了他的理解力。关于这一点,诠释者说:对一件事的正确理解与对同一件事的误解,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但无论如何,必须假定这种头脑简单和自大削弱了对那入口的看守,就算是以微不足道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那个守门人性格上的缺陷。再加上那个守门人似乎生性和善,并不总像个公职人员。
在故事一开始,他就开了个玩笑,邀请那人不顾明确的禁令而进入,然后他没有马上赶他走,反而如文中所述给了他一斟凳,让他在门边坐下。在那么多年里,他展现耐心,忍受那人的央求,进行小小的审讯,接受礼物,宽宏大量地容许那人在他旁边大声咒骂那不幸的巧合,是巧合把那守门人置于此地——这一切都可归之于他动了同情心,并非每个守门人都会这么做。最后在那人向他示意之后,他还深深朝那人弯下身子,给他问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从‘你总是不满足’这句话中只流露出些许不耐——守门人知道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有一种诠释甚至更进一步表示,‘你总是不满足’这句话表达出一种友好的赞叹,而此一赞叹并非没有高高在上的意味。总而言之,守门人这个人物的塑造与你所想的不同。”
“你比我更熟悉这个故事,也知道得比我更久,”K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K说:“所以你认为那个人并没有被欺骗啰?”“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神父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针对这个故事有哪些看法。你不必太在意这些看法。写下来的文字不会改变,而看法往往只表示出对此的绝望。就这个故事来说,甚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个守门人才是被欺骗了的人。”“这个看法扯得太远了,”K说,“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守门人的单纯,”神父说,“有人说他并不识得法律的内部,只识得入口前那条路,他必须一走再走的那条路。他对法律内部的想象被视为天真,而且有人认为他自己也畏惧他想让那人感到畏惧的东西。可以说他比那个人还要畏惧,因为那人一心想要进去,就算听说了里面有更可怕的守门人,而那个守门人却并不想进去,至少故事里没说他想进去。虽然也有人说他一定去过里面,因为毕竟他曾经被法律任命担任此一职务,而此事只可能在里面发生。
另一些人对这个说法的回答是,他也可以透过从里面发出的一声呼喊而被任命为守门人,至少他应该不曾进到里面的深处,既然他连第三个守门人的模样都已经无法忍受。此外,故事中也没有提到在那许多年里,他还叙述过什么关于里面的事,除了针对里面那些守门人所说的那番话之外。也许他被禁止叙述,但他也不曾提起这个禁令。有人根据这一切推论出,他对那里面的样子和意义一无所知,有的只是一种错觉。据说他对那个乡下人其实也有一种错觉,因为他从属于这个乡下人,而他并不知道,反而把乡下人当成下属来对待,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你应该还记得,但他其实是从属于乡下人的。根据此一看法,守门人从属于乡下人这一点在故事中也表现得很清楚。
首先,受束缚的人从属于自由人。而那个乡下人的确是自由的,他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只有法律的入口不准他进入,而且只被一个人禁止,亦即那个守门人。如果他在门边那斟凳上坐了一辈子,那么这是出于自愿,故事里没有提到他受到强迫。然而守门人却由于自己的职务而被束缚在他的岗位上,他不能离开,看样子也不能进去,就算他想要进去。此外,他虽然是为法律效命,却只为了这一个入口效命,也就是说只为了这个乡下人,因为这个入口就只是为了此人而设。基于这个理由,他隶属于此人。可以假定,在那许多年里,在整个壮年时期中,在某种意义上,他只执行了空洞的职务,因为文中说,一个男子来了,指的是一个壮年男子,这表示那守门人在履行义务之前得要等很久,而且所等待的时间是由那个男子决定的,毕竟他是自愿来的。而这份职务的结束也是由那个男子的结束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直到最后他都隶属于那个人。而且文中一再强调,守门人似乎对一切都一无所知。
不过,这一点并不引人注目,因为根据此一看法,守门人还有一种更严重的错觉,此一错觉涉及他的职务。因为,最后他提到那个入口时说:‘现在我要走过去把它关上’,可是在一开始时提到过通往法律的那扇门始终是敞着的,而那门若始终是敞着的,‘始终’表示不受限于那人的长度,虽然此门是为了那人而设,那么就连守门人也无法把门关上。
那守门人之所以宣布要去把门关上,只是想给一个回答呢,还是想强调他的职责呢?还是在最后一刻想让那人陷入悔恨和悲伤?关于这一点,大家意见分歧。但是许多人一致认为守门人无法把门关上,他们甚至认为他的知识也在那人之下,至少是在最后,因为那人看见了光从法律的入口透出来,而负责看门的守门人想来背对着入口站立,而且从他所说的话当中也不曾显示出他察觉到此一变化。”
“这很有根据。”K说,他小声地复述着神父所做说明中的一部分。“这很有根据,现在我也认为那个守门人被骗了。但是我并未因此放弃我先前的看法,因为两者并不冲突。那守门人究竟是把事情看得很清楚,还是被骗了,这一点无法判定。我先前说那个人被骗了。如果守门人把事情看得很清楚,那么就可以怀疑我的说法,可是如果守门人被骗了,那么他的错觉就势必会传染给那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守门人虽然不是骗子,但却如此头脑简单,应该立刻就被免职。毕竟你得考虑惮守门人的错觉对他自己没有损害,对那个人却有千百倍的损害。”
“在这一点上,有人与你意见相反,”神父说,“因为有些人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评断那个守门人。不管我们怎么看他,他都是法律的仆人,听命于法律,亦即脱离了众人的评断。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能认为守门人隶属于那个人之下。由于他的职务,哪怕只是被束缚在法律的入口,还是远胜于自由地生活在世上。那人才到法律这儿来,守门人就已经在那儿了。他是由法律任命来担任此一职务的,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律。”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K摇着头说,“因为如果同意这个看法,就得把守门人所说的一切视为真实。但这是不可能的,你自己就详细地陈述过理由。”
“不,”神父说,“不必把一切都视为真实,只需要视之为必要。”“令人沮丧的看法,”K说,“谎言成了世界秩序。”
K将这句话作为结束,但这并非他的最终评断。他太过疲倦了,无力综观由这故事所引申出的所有结论,而且这故事带领他进入不寻常的思维逻辑,不真实的事物,比起他来,更适合由一群法院公务员来探讨。这个简单的故事变得奇形怪状,他想把这个故事拋在脑后,而神父十分体谅地容忍K这么做,默默地接纳了K的意见,尽管这意见跟他本身的看法肯定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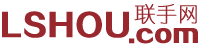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1002014640号 浙ICP备11030581号-3
浙公网安备 33011002014640号 浙ICP备11030581号-3